资讯分类
8.7分算神剧吗?道尽了东亚家庭的权力结构 -
来源:爱看影院iktv8人气:262更新:2025-09-18 02:24:15
观看《有生之年》前四集的体验,如同漫步台北街头品尝珍珠奶茶般平凡而温馨。这种茶水虽不昂贵,却能轻易获得的微小幸福,恰似台湾本土文化孕育的独特产物。难怪不少内地观众对剧中「生活流」呈现的悬浮感产生质疑:为何即将迈入而立之年的青年能安心于家庭早餐店的帮工岗位?为何中年主妇在连锁快餐店打工仍能保持从容?为何年迈母亲面对儿子餐馆投资失败的惨状依然情绪平稳?为何这些角色普遍缺乏高学历与高收入却毫无焦虑?这些问题背后,实则是对台湾社会现实生态的深刻映射。

《有生之年》所引发的争议毋庸置疑,但剧作本身并无瑕疵,其独特性恰恰源于截然不同的文化语境。在该剧上线首周,相较于《三联生活周刊》一篇以冷静笔触描绘当代大学生困于考研考编循环困境的特稿,社交媒体上的讨论热度明显偏低。该特稿精准捕捉到一个被学历门槛、体制规则与世俗标准共同塑造的群体画像,在"上岸"信仰盛行且焦虑蔓延的社会氛围中,观众反而将《有生之年》中看似琐碎的生活细节视为理想主义的避风港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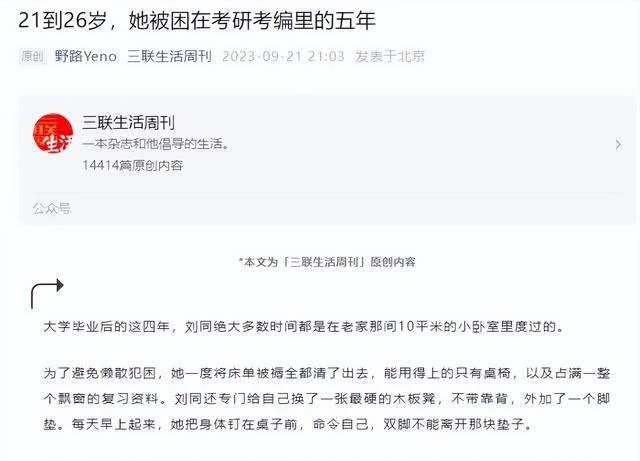
三联特稿「有生之年,能长这么大,算不错了。」故事始于41岁的高嘉岳在绝境中萌生的死亡念头。他经营的屏东琉球乡小饭馆破产,多年女友却怀了他人的孩子。人到中年,高嘉岳仿佛被命运施了魔咒——任何事情都难以坚持到底,连结束生命的想法也难以实现。这个被世俗定义为失败者的浪荡子,既无法好好活着,又无法痛快死去,最终成了困在夹缝中的矛盾体。在彻底绝望的夜里,他烂醉返乡,试图为自己策划一场告别的聚会,却意外撞入了家人混乱的生活场景。他发现,不仅在异乡浮沉,故乡的亲人同样活得狼狈不堪。父亲知晓长子酗酒的劣迹,担忧他沉睡时可能窒息,整夜守候在侧。这个表面操劳的父亲实则极度自我,对同居的妻儿缺乏共情,每日执着于喂养家禽家畜,却无法给予妻子情感慰藉。他对小儿子的颐指气使,相比之下,对年轻保健护士的艳羡更是微不足道。

母亲将半生岁月付诸于琐碎的操劳,在与丈夫共同经营早餐店的漫长岁月里,用双手支撑起整个家庭的生计。当三个子女陆续成年,她本该享受到天伦之乐,却在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中,与丈夫的情感逐渐疏离。老宅狭小的空间里,母子三人被迫共享一室,母亲虽渴望逃离这种束缚,却因经济依赖与心理惯性而难以割舍。她以暴躁怨妇的姿态对抗现实,却无形中将全家拖入更深的困境。老二看似完美地扮演着儿子、兄弟、丈夫与父亲的角色,殊不知他过度迁就的付出正悄然践踏着家人的真实需求。而老三作为典型的「全职儿子」,在父母的庇护下延续着孩童般的依赖,三人如同身处同一屋檐下的陌生人,彼此熟悉却难以真正理解。

在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,人们习惯佩戴面具守护各自隐秘的角落。高嘉岳带着最深沉的秘密返乡,如同孩童戳破皇帝新装的谎言,在不合时宜的时刻掀开被刻意掩饰的真相。这个家庭里,唯有高嘉岳始终与时代脱节,既非成熟稳重的成员,也非能维持和谐的纽带。老高家尔虞我诈的相处模式,折射出典型的东亚式家庭困境。而《有生之年》的剧本创作显然未能突破这一框架,既未呈现出新的观察视角,也未塑造出鲜活的人物形象,其叙事方式终究仍困于套路之中。

从前三集的剧情发展来看,大量情节走向具有明显的可预见性,编剧的叙事策略往往缺乏新意。例如,侄子在网恋见面时让大伯代为承担,结果对方女生对大伯产生好感;侄子协助爷爷寻找物品时意外发现大伯的遗书,为"拯救"大伯擅自撮合其与网恋对象;而大伯曾深藏心底的初恋,竟意外成为老三的女友。这些刻意设计的巧合不断推动剧情发展,却用套路化的桥段消解了戏剧张力。编剧在构建"戏剧真实"时显得力不从心,但该作品仍能在程式化的情节框架中,捕捉到东亚家庭内部微妙的权力博弈。例如,离家出走的父亲在母亲旅游期间突然归来,径直质问小儿子"谁给你做饭";大儿子目睹母亲拆快递时,本能反应是责怪其"网购太多浪费钱";母亲试图与小儿子分享旅行中的喜悦时刻,却遭到来电即刻汇报父亲近况的冰冷回应。这些看似随意的细节处理,恰恰揭示了家庭关系中隐形的等级秩序,让观众在套路中感受到真实的伦理困境。

最具感染力的还是演员们将文本细节转化为视觉体验的能力。若将剧作比作一幅画的「骨相」,仅四集的体量尚不足以断定其骨骼结构是否稳固。但其「皮相」已显现出鲜明的质感——杨贵媚与吴慷仁的演技如同定海神针,只要他们入镜,便为整部剧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。当演员元素被抽离后,剧中角色呈现出典型的当代生活图谱:老大提供短暂的情绪慰藉却常制造麻烦,他的洒脱背后藏着无数补救;老二看似周到却暗藏疲惫,周围人同样被其负担压得喘不过气;老三缺乏人生目标,更像是被母亲牵着走的影子;老爹则是家庭权力的核心,而母亲则在压抑中艰难求生。这种类型化的角色设定让观众产生强烈共鸣,却也导致人物形象趋于扁平。

这部剧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演员们精准的诠释,他们以独特的个性为角色注入生命力,在表演中赋予人物鲜明的辨识度。剧中呈现出「生活流」与「悬浮感」的微妙平衡,后者源于情节设计的过度套路化,而前者则由演员的演绎完成。吴慷仁饰演的高嘉岳极具张力,他以醉酒后的张扬拥抱久别亲人,用失控的肢体语言释放压抑情绪,看似放纵的欢乐实则掩盖着孤立无援的悲凉。在充满秘密的家族中,他恰恰是秘密最深的守护者。吴慷仁敏锐地把握着表演尺度,在「大于生活」的戏剧性中保持着恰到好处的克制,完美演绎了悲伤小丑的复杂性格。相较之下,郑元畅则以细腻的表演方式呈现现实质感,他淡然应对各种戏剧冲突,尚未褪尽的少年气质与演员包袱反而成为点睛之笔,二哥角色在生活剧场中化身谨言慎行的「理想化身」。

杨贵媚的角色最为丰满,她每一次在画面上的出现都在重新诠释着生活的本质,甚至以一种尖锐的方式叩问着生活本身。从「假靳东」到「秀才事件」,这些情节将缺爱的东亚老年女性推上了舆论的风口,而话题的喧嚣之下,实则隐藏着无数在情感困境中挣扎的具体个体。《有生之年》中,杨贵媚所演绎的高妈妈形象,既是对「社会话题」的突破,也是对东亚母亲群体深刻而复杂的写照。她用泼辣与怨怼、爆发与隐忍,将几十年家庭生活的压抑与矛盾具象化为一个鲜活的符号。当观众惊叹于她如何将「高妈妈」这一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时,更应注意到她身上承载着无数相似命运的女性影子。尽管故事主线围绕高嘉岳展开,且他注定成为剧中焦点,但观众内心深处始终期待着镜头能更多地聚焦于杨贵媚。我们渴望见证她从高妈妈的桎梏中挣脱,化身为独立的陈大姐,成为一个不再依附于任何男性角色的完整个体。这或许才是《有生之年》最值得期待的升华——让杨贵媚的旅程超越短途的乡愁,走向更广阔的生命可能。然而,当高嘉岳踏上返乡之路时,我们不得不警惕,这种叙事是否可能再次落入男性中心的窠臼,将女性的困境简化为「乡愿」的陈词滥调?

《有生之年》的开场画面以水下视角展开,琉球乡近海的澄澈水质宛如琉璃,庞大的海龟在清澈的水域中悠闲游动。在与侄子交谈时,高嘉岳提及这一画面曾在他曾试图自杀未遂的时刻浮现。

这段充满浪漫气息,甚至略显过度的描述,使《有生之年》呈现出一种经过创新的新型偶像剧形式。它摒弃了那些虚幻的空中楼阁式的表演,转而将生活中的阴暗面以浪漫笔触呈现。与其归类为传统台剧的「生活流」,不如将其视为偶像剧类型在叙事上的突破——通过吸纳失败者的故事,用戏剧化的现实为真实人生披上糖衣,创造出别具一格的观剧体验。
最新资讯
- • 《问心》口碑两极化,医疗剧还有“救”吗? -
- • 《繁城之下》定档10月13日,白宇帆宁理共解谜案思辨人性弧光 -
- • 一集飙上9.7!这顶级尺度,在国内肯定被封杀! -
- • 《彗星来的那一夜》, 我们试图在寻找一个答案 -
- • 25年后,再看张艺谋与巩俐的这部电影,我仍旧不寒而栗 -
- • 票房不该这么少,《志愿军》对比《长津湖》,五个地方更优秀 -
- • 惊心动魄,网飞最新复仇爽片,看韩国美女如何虐杀整个黑帮 -
- • 张颂文也救不了《志愿军》?票房爆了,但观众的弃片理由却很一致 -
- • 《长空之王》试飞员的生死瞬间!王一博胡军惊险刺激的航空冒险 -
- • 王宝强执导《八角笼中》,由真实故事改编,感人至深的命运之路 -
- • 两个嚣张的老父亲,折射出《坚如磐石》的全部用心 -
- • 请把「邪神」洛基还给我们 -
- • 成毅、李一桐二搭,《狐妖小红娘王权篇》启动,王权富贵霸气来袭 -
- • 《知否》海氏聪明贤惠,长柏娶她是高攀,大娘子为何不乐意? -
- • 《兰闺喜事》锦荣想嫁豪门,除门不当户不对外,有三难! -
- • 《烬相思》定档,宋伊人王佑硕主演,女强男弱,青年甜宠剧 -
- • 好家伙!赵又廷新剧刚开播就被五星刷屏,观众的好评理由出奇一致 -
- • 收视率高到“吓人”的6部剧,部部是经典,你熬夜追过哪部? -
- • 张嘉益《欢乐家长群》将袭,全员演技实力派,生活剧有盼头了! -
- • 特工任务:大结局姚瑶打入夜雾核心,黄子诚假死,高天阳继续潜伏 -